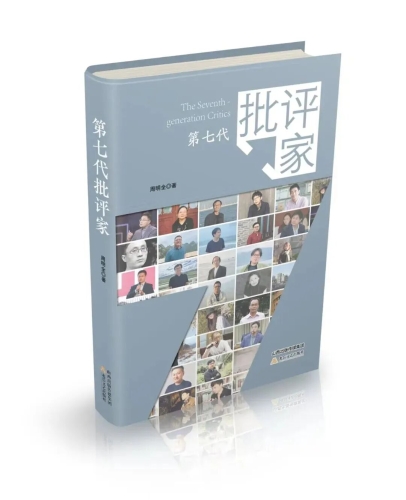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家》杂志主编周明全所著的《第七代批评家》以对话形式深度访谈了24位在不同批评领域做出引领性批评成果的第七代批评家代表,在有锐度、有深度、有温度的对话中,关注批评的读者能够在新时代变化多端的批评语境中洞见批评的坚守与突围,也能够触摸到第七代批评家火热跳动的批评特质与思考。作者周明全对不同代际或者说不同时代的代表性批评家的研究可谓手拿把掐、信手拈来,他著有《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与陈思和共同主编《80后批评家文丛》《70后批评家文丛》,主编《当代著名学者研究资料丛书》等,他也一直关注研究批评的时代之问、方法之问、未来之问……。欣欣然沉浸式阅读中,在《第七代批评家》中可以看见当下批评的清晰鲜活图景,听见人文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对批评本质与价值的追问,更能预见当代批评的前路方向。
一、 批评家身份突围
批评家批评身份与时代、作家、作品、个人学识、审美趋向等众多因素血肉相连,书中对话批评家的简介就旗帜鲜明地展示着第七代批评家的批评身份,某种侧面也代表了批评的话语权与权威性。书中提出“第七代批评家”的概念,本身就是对传统代际划分模式的突破。对话中,杨庆祥指出“以年龄来划分批评家是不科学的”,围绕是否共享“重新认识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学”的问题意识,他建议用“第七代”替代年龄标签,这种对代际标签的审慎,恰是第七代批评家的清醒之处:他们拒绝被年龄绑架,更强调以“问题”为纽带的群体凝聚。
书中对话第一个问题聚焦的是少有人关注提及的批评机制、平台、批评场域等问题。沿着第七代批评家群体亮相的批评脉络,可以探寻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机制、《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等平台为第七代批评家提供的“对话场域”。刘大先回忆,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后,“不同背景和学术倾向的同代人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情感、思想与观点上的交流与碰撞”,这种良性生态让批评摆脱“散兵游勇”状态,也没有陷入“圈子化”的封闭;张莉提到,作为首届客座研究员,定期研讨“逼迫我去迅速了解当代文学现场,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这种“集体性”更多是为批评赋能,而非身份绑定。
值得关注的是,第七代批评家的代际意识中,始终蕴含“去中心化”的自觉,他们批评的维度多元开阔,针砭时弊。金理在讨论“新东北作家群”时,反对将东北作家群代表性作家双雪涛、班宇等作家的创作简单归因于“地域”,主张“在古今中西纵横交融的立体视域中发现传统、审视传统、扬弃传统”;黄平则强调“东北”对他而言是“阶级范畴”的隐喻,而非地理概念,其研究指向的是“下岗一代的尊严”这一普遍性问题。这种对“单一维度”的警惕,让第七代批评家的群体特质不流于表面,而是深入到问题意识的层面——他们以“代”为契机,却最终超越“代”的限制,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植根传统深度中对话。
批评家身份的突围,本质上是对批评视野与批评维度的深度探索与思考。
二、 批评的守正创新
新时代重大叙事语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反复强调守正创新,批评也如此,批评在坚守最基本的批评原则与立场的同时,也需与时俱进。第七代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始终围绕“文学批评的本体性”展开,既坚守传统批评的核心价值,又积极拓展批评的边界与形式,让批评在守正创新中活起来。
第七代批评家普遍认同的批评的“守正”在于对文本细读与真诚立场的坚守。第七代批评家普遍反对以理论框架强行套取文本,或用流量逻辑替代审美判断。张定浩主张批评应先“虚心涵泳,充分体味作品自身”,再“先信后疑”,避免“为批评而批评”的偏执;岳雯则将“道德”视为批评家的底线,认为“对于批评家,道德是第一位的”,这种道德是“言行一致”的真诚,而非应付考核的“门面话”。李遇春强调“文学批评是科学研究而不是文学创作”,主张“史证”“心证”“形证”的“三证合一”,从文本形式出发,挖掘其社会历史与精神心理内涵,避免“过度阐释”。
第七代批评家普遍认同的批评的“创新”体现在批评视野的拓展与文体的突破上,他们认为批评对象上,要将网络文学、科幻文学、非虚构写作等纳入研究范畴。杨庆祥主编“青科幻丛书”,试图通过科幻文学“拓展我们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他后续对科幻写作“同质化、缺乏探索精神”感到失望,却仍认可其“重新定义时间和世界”的可能性;金理关注“非虚构中国和中国非虚构”,他在“双城文学工作坊”中邀请记者、人类学家参与讨论,打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壁垒;何同彬则反思“青年写作的大学化”困境,主张作家应“意识到大学化的局限,丰富和拓展更多的经验”。这些批评的创新实践表明,第七代批评家不再将文学局限于传统文体,而是将其视为观察社会、反思时代的重要载体。
批评的守正创新,始终与时代与现实同频共振。
三、 批评出路之思
在当下批评众声喧哗、五花八门的时代语境里,《第七代批评家》深广兼备对话讨论学院体制、市场逻辑与媒介变革带来的多重挑战,也从对话批评家的批评历程、学术背景及深邃思考中,扫描探照批评的未来出路。
批评界一直有关于学院派批评的讨论与论争,貌似批评的话语权绝大部分掌握在学院派批评手中。对话的第七代批评家有学院高学历教育背景,绝大多数还在“学院”任职,他们对学院派批评有切身体会,也有真知灼见,更对批评的出路有持续深思。李遇春直言“学院批评在过于僵化的高等教育评价机制的支配下生存受到了严峻挑战”,“C刊体”让批评文章“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整齐划一”,甚至“不能写‘我’只能写‘笔者’”,文学批评的个性与温度被逐渐消解;王晴飞则指出,高校评价体系中“文学批评的重要性会低于文学史研究”,甚至“批评文章不被计入考核成果”,导致年轻批评家不得不“在学术与批评之间游走”,牺牲批评的现实关怀以迎合体制要求。
带着对批评烛照出路的思考,第七代批评家也给出了自己的解答。黄德海主张“就改善你自己好了”,将精力集中于自我提升,以独立思考对抗外部规训;丛治辰则选择“尊重前辈,做青年;尊重世界,做自己”,在适应体制的同时,坚守批评的学术底线与现实关怀;李遇春则通过“重建批评的学理性和有效性”,试图让学院批评“针对当前的文学创作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沦为“形式主义的花样文章”。
面对批评面临着的“娱乐化”与“利益化”风险,何同彬批评当下文学界的“媚少”现象——部分刊物为吸引流量,“疯狂地抢青年作家的稿子”,甚至降低稿件质量要求,导致“我们的文学正在失去年轻的力量和青年的气质”;岳雯则指出,自媒体时代的“热搜逻辑”让批评沦为“事件化”的附庸,“真正的文学价值反而被遮蔽”。金理强调“抛开工作量、学术考核的各种现实的、功利的考虑”,拿出“自己满意的专著”,甚至为青年学者争取“不掏腰包、不靠经费资助且能有版税收入”的出版条件,以对抗出版市场的利益逻辑。
面对新媒体崛起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与挑战,第七代批评家也摆明了批评态度。黄平在B站开设账号,将学术内容转化为视频,践行“把论文写在B站上”的理念;杨庆祥参与“文学脱口秀”,尝试以娱乐化形式传播文学观念,也坦言“这个节目还是放不下身段,还不够脱口秀”,警惕批评沦为纯粹的娱乐;霍俊明主持“中国好诗”“天天诗历”等出版计划,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平台推广诗歌,让批评更贴近大众。丛治辰认为批评“应该有它的尊严和品质”,不能为适应媒介而丧失思想深度;王晴飞则强调“出圈”的前提是“在圈里”,批评家应“先把自己安身立命的工作做好”,再谈“把圈内的美好风景带给更多人”,避免“没入门”却谈“出圈”的浮躁。
批评出路,每代批评家有各自的探索解答,路总会有的。
在与第七代批评家对谈共话碰撞交流中,可以洞见他们对“批评尊严”的坚守与“公共性”的担当。这种坚守与担当,既体现在对文学本质的认知中,也落实在具体的批评实践里。纵览全书可以洞见第七代批评家始终保持“自我反思”的自觉,他们始终以谦逊的态度面对批评、面对文学。从最后一个对话问题“若给批评家朋友或晚辈推荐几本书,你会推荐哪几本?”回答中,可以洞见第七代批评家的批评态度与见解,给批评者更多启示思考。
周明全所著的《第七代批评家》在温润深入的对话中,用第七代批评家的批评话语场与智慧哲思回应了当下批评的困境,也开拓了未来批评广阔空间。第七代批评家也始终以“真诚”与“敬畏”为底色,重建着批评的尊严与价值,为批评画出了底线。正如於可训在代序中所言,周明全等批评家“有古圣先贤的遗风”,在“博观”的基础上“圆照”研究对象。如果是批评爱好者、批评写作者,《第七代批评家》一定会是洞见批评本质的最为好读易读的读本,有没有收获,有没有启发,其义自见。